这件丢人的事,算是我最不愿触碰的过去。
汶川地震那时,我高一。
那时,身边的同学们都唏嘘感叹不已,不少也被这悲痛感染。但是,我则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刺激得兴奋难眠:
我要效仿电视和报纸的案例,在学校举行一次烛光祈福会。
一个同样好事的同学和我一拍即合,我们开心地骑车去交易场,自费采购了一批小蜡烛。
那天天气很好,和风徐徐。路边橱窗里电视中紧张的救援行动牵引着人们的神经,而我们俩满载而归,一路欢声笑语。
该摆什么样的形状呢?是汶川二字,还是中国加油,还是偌大一枚爱心?我和他认真地规划着,恨不得天早点暗下来,点燃我们的满心期待。
那个灾区女记者的采访中,目送着失去全部亲人的踽行老人消失在地平线,她突然蹲下来哭了,被直播到电视上。而我们此时二人忙得满头大汗,无意中流到唇边的汗水,仿佛也是甜蜜的。
天终于黑了。晚自习还没结束,我和他不顾老师的目光,骄傲而兴致盎然地带着蜡烛下了楼,仿佛早就被授予了某种特权。有些同学也听说了我们的计划,叽叽喳喳一般,怀着同样的高昂兴致,随着我们下楼摆蜡烛去了。
我们一群人有说有笑的,谈论着今天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轰动。
有个母亲,为救自己年幼的孩子,用肉体支撑起一个狭小的空间。孩子获救,母亲却去世了。这件事我们第一时间就从新闻上获得,大家没人说什么,心中却盘算着是否可以加入作文。果然,期末考试中有不少人都用到了这个题材。
在意料之中,我们吸引了全校的目光。亮橙色的烛光摆成巨大的爱心,中间有5.12字样,在暗夜之中闪烁着,尤为醒目,暖暖地照亮了围观群众们或好奇、或兴奋、或复杂的面庞。而旁边的教学楼上,也挤满了围观的高二高三学生,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标配着当时颇为时髦的能拍照的手机,静静期待着。
我的嗓门不大,人一多,声音就被淹没了。那时我班上的死对头站了出来,替我起了国歌的头,然后,全校的围观群众们陷入了国歌的大合唱。
我对他是又感激,又愤恨。感激他解了围,不至于让烛光会失去控制,愤恨他抢了我的风头,让人忘记了谁才是领导者。
接着,我班上的一位亲密好友也自告奋勇站了出来,用她洪亮的嗓门起头了《五星红旗》,然后,恢弘无比的大合唱又再次扫荡骚然的校园。
这回,我对她只有愤恨了。
许多人眼睛已闪烁着泪光,可嘴角的弧度泄露了他们情感的颜色。
不断有人加入围观,不断有拍照的咔嚓声响起。
但总体来说,我们两个组织者还是很兴奋和开心的,我们成功举办了这么大的祈福会,我们吸引了那么多的目光,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肯定!
甚至到了后期,我已经不注意是否还是风头中心了。忙前忙后,用打火机补齐熄灭的蜡烛,争做无名英雄。我的自豪感升腾而起,把我的心灵占据得满满的。。。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可是长大了些的我,还是无法忘记自己昔日堂而皇之消费国难换取注视的行为是如此的可耻。那费而无用的祈福会,因套上了道德的袈裟,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放下心防的拙劣社交。集体主义和形式主义从小在我们幼嫩的心灵中沉积,发酵出恶臭的烟雾,却把每个人都熏得流下感动泪珠。
大学时,我学到了个词,叫刻奇(kitsch,被自已的行为所感动,自我愚弄。谈客注)。这个音译词如同一个巨大耳光,更让我无法释怀心中的羞耻。
每当我看到国灾大难后华而不实的祈福、假脸遍布的晚会,我都不得不揣测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动机,虽然,他们宣传的动机听起来总是那么神圣,那么无私。
是的,当时,我也以为我是神圣而无私的。后面发现,我的神圣无私仅价值35块,即蜡烛钱,比我的捐款还多。
那天的烛光晚会还上了本地的电视台,忘记是谁打电话去爆料的了。
可是,灾区人民会看得到这小电视台的报道吗?他们看了会欣慰万分吗?会因欣慰而忘却失去一切的痛苦吗?会感激默默无闻的我吗?
我那时哪有想这么多啊。
这是我做过最坏的事。
之所以你们觉得不够坏,是因为你们低估了这类事情的恶性。以善为画皮行的恶事、虚伪事,对社会与人心的腐蚀更甚于那些看得到摸得着的物理损害。
读了这个故事,你是否有同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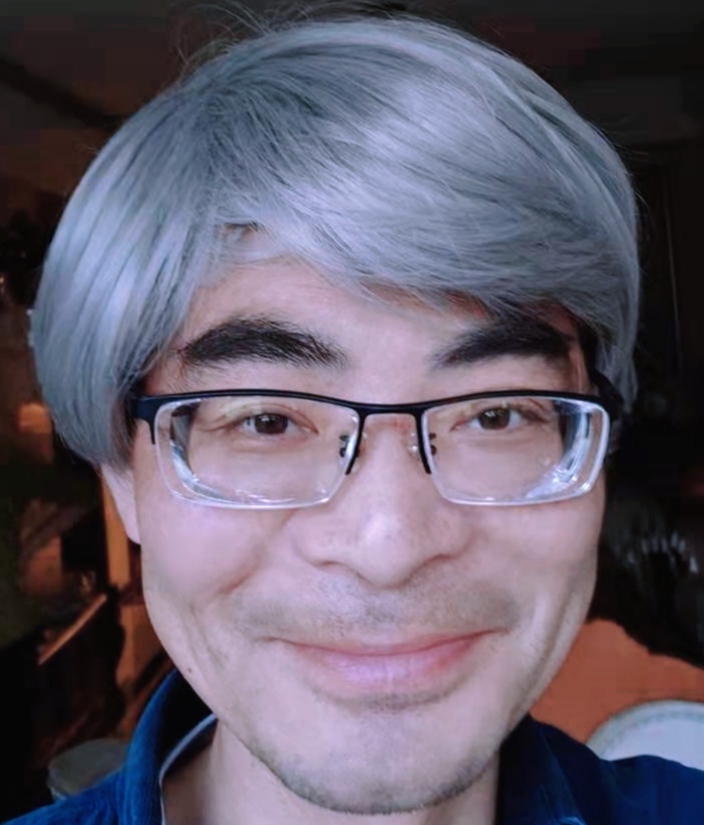
最新回复